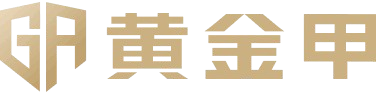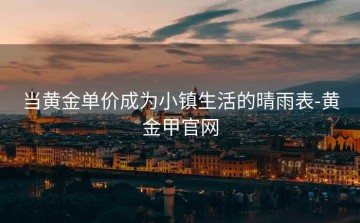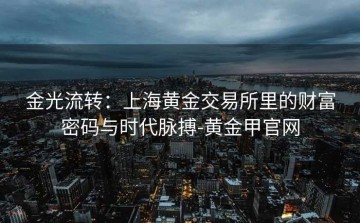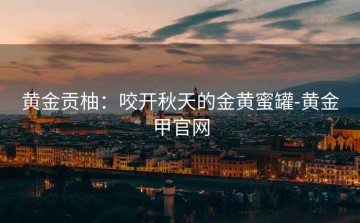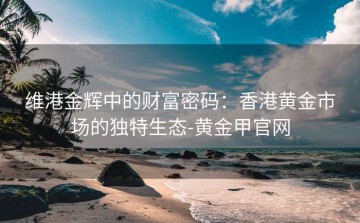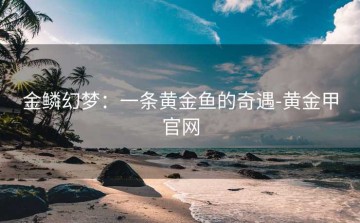熔炉里的金色诗篇:黄金提炼的隐秘旅程-黄金甲官网
当第一缕晨光刺破矿场的薄雾,老张蹲在熔炉前,指尖抚过冷却后泛着柔光的金锭。这团金属曾深埋地下亿万年,经他手完成从矿石到纯金的蜕变——那不是冰冷的化学反应,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一段熔铸文明的史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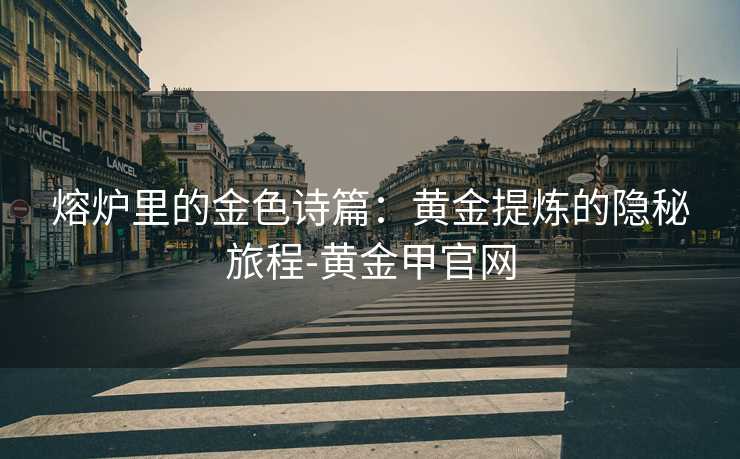
一、历史的火种:从砂砾到王冠
早在公元前3000年,古埃及人便掌握了“砂金收集术”:他们用羊皮袋装满含金砂砾,在尼罗河畔反复拍打,让比重大的黄金沉入袋底。这种原始方法像婴儿学步,却开启了人类对贵金属的痴迷。后来,中国人发明了“灰吹法”——将金矿石与铅混合熔炼,铅吸收杂质后氧化成灰烬,留下的便是“狗头金”。宋代《天工开物》记载此法时,称其为“以铅为媒,取金于灰”,恰似用生命为代价,从混沌中剥离光明。
中世纪的欧洲,炼金术士们则把黄金提炼推向神秘主义。他们在坩埚里混合硫磺、水银与矿石,吟唱咒语 hoping 点石成金。尽管从未成功,但他们无意中改进了蒸馏与提纯技术,就像诗人误打误撞写出千古绝句——失败的过程里,藏着突破的密码。
二、技术的淬炼:从汗水到精度
现代黄金提炼早已脱离巫术,成为精密的科学。在南非的金矿深处,工程师们用“氰化法”处理低品位矿石:将矿石粉碎成粉末,浸泡在含氰化钠的溶液中,黄金离子与氰根结合成稳定的络合物,再通过活性炭吸附回收。这一过程像一场 molecular 芭蕾,每一步都需要严格控制pH值与温度,差之毫厘便会前功尽弃。
更神奇的是生物提炼法:科学家培养嗜金菌,让它们吞噬矿石中的硫化物,释放出包裹黄金的微粒。这些“微型矿工”在35℃的恒温箱里工作,24小时就能完成传统方法一周的任务。老张参观实验室时,望着试管中蠕动的菌群,忽然想起祖父说的:“最好的提炼师,要学会向自然借力。”
三、精神的熔铸:从杂质到纯粹
黄金的珍贵,一半在物理属性,一半在人文寓意。提炼过程中,“除杂”是最动人的环节:当熔融的黄金倒入模具前,工人会用硼砂去除残留的银、铜杂质——那些闪着异光的金属,曾是矿石中最顽固的“叛逆者”,却在高温下屈服,化作一缕青烟消散。这多像人生的修行:唯有剔除浮躁与杂质,才能接近本质的纯粹。
去年,老张参与了一项“环保提炼项目”。他们用离子交换树脂替代氰化物,虽然成本高了两倍,却能避免剧毒废水污染河流。当他看到冶炼厂下游重新出现嬉戏的鱼群时,忽然懂了:黄金的价值,从来不只是价格标签上的数字,更是人类对平衡与责任的坚守。
如今,老张的书桌上摆着两块金锭:一块是早年用传统方法炼出的,表面带着粗粝的划痕;另一块是用新技术制成的,光滑得能映出人影。他说:“前者像我的青春,跌跌撞撞却有温度;后者像现在的自己,精准却少了些烟火气。”但无论哪种,都是时光的馈赠——黄金提炼的本质,从来不是征服自然,而是在熔炉的呼吸中,读懂文明的脉搏。
当最后一缕火焰熄灭,金锭躺在模具里泛着冷光。它不再是地下的矿石,而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凝结。这场从砂砾到王冠的旅程,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,续写新的金色诗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