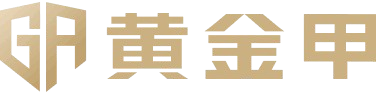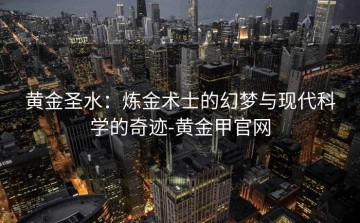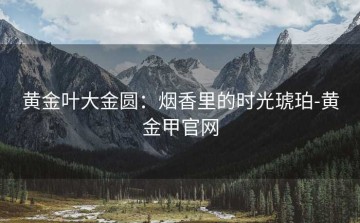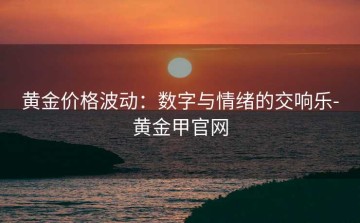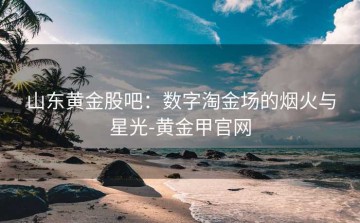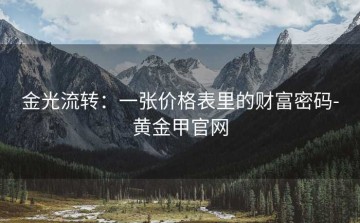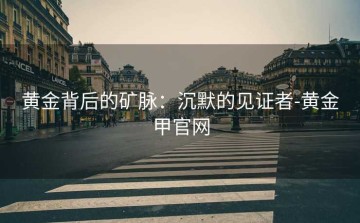铅字织就的时代星图:黄金时代小说的精神漫游-黄金甲官网
黄金时代小说,是特定历史维度中,作家们以笔为舟、以纸为岸,在时代洪流里打捞的精神碎片。它们不是冰冷的文字堆砌,而是带着体温的对话——与时代对话,与人性对话,与每一个渴望理解世界的灵魂对话。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纸页,仿佛能听见鲁迅笔下狂人的呐喊,看见巴金笔下觉慧冲破牢笼的身影,触摸到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心跳。这些作品如同散落在时间里的星辰,虽历经岁月侵蚀,却始终闪耀着思想的光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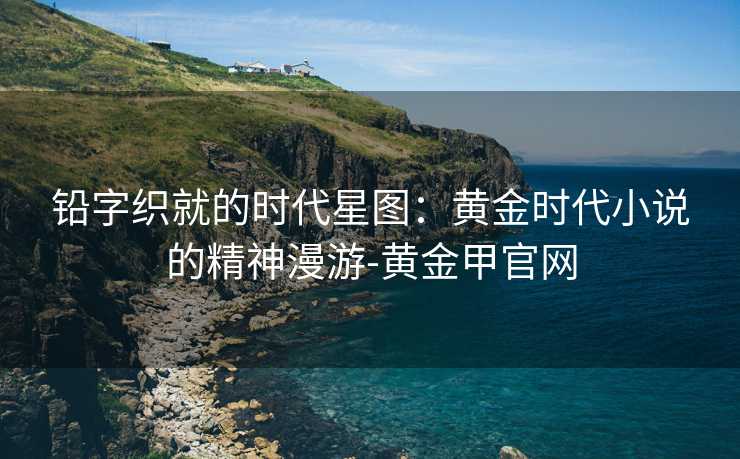
一、现实锋刃与理想火种:黄金时代的双重底色
黄金时代小说的魅力,在于它兼具现实的锐利与理想的温度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以“吃人”二字撕开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,让无数人惊醒于时代的麻木;《家》中的觉慧挣脱高家的枷锁,奔向未知的远方,象征着青年对自由的渴望;而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则以诗意化的笔触,构建了一个纯净的乌托邦,在战乱年代为人们保留了一片心灵的净土。这些作品没有回避时代的苦难,却在苦难中点燃希望的火种,让读者在黑暗中看到光的方向。
这种“痛并希望着”的张力,正是黄金时代小说的灵魂。茅盾的《子夜》中,吴荪甫的雄心与失败,折射出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挣扎;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里,祥子的三起三落,写尽了底层人民被命运碾压的无奈。作家们不美化苦难,也不消解抗争,而是在残酷现实中挖掘人性的韧性——就像巴金所说:“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,而是因为我有感情,我要把我的心里话告诉别人。”
二、艺术实验与文体自觉:黄金时代的创新基因
从艺术层面看,黄金时代小说的创新同样令人惊叹。张爱玲将上海滩的繁华与衰败揉进《倾城之恋》的字里行间,用冷峻的笔调剖析人性的幽微;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以北京方言勾勒出底层车夫的悲剧人生,让市井气息扑面而来;郁达夫的《沉沦》则大胆袒露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,开创了自我抒情的现代小说传统。作家们各展所长,或写实或抒情,或批判或歌颂,共同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学图景。
更可贵的是,黄金时代小说的“新”,并非为了标新立异,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时代精神。比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,用散文化的结构讲述东北农民的苦难,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,却让生命的沉重感更具冲击力;钱钟书的《围城》,以辛辣的讽刺解剖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,用“城里的人想出去,城外的人想进来”的经典隐喻,道尽人生的荒诞。这些创新不是孤芳自赏,而是为了让文学更贴近人心。
三、大众共鸣与永恒价值:黄金时代的当代回响
最重要的是,黄金时代小说从未脱离大众的生活。它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书写小人物的生存困境,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、《孔乙己》中的酒客、《雷雨》中的鲁侍萍,这些角色不再是遥远的符号,而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同类。他们的痛苦与挣扎,正是时代的缩影;他们的觉醒与反抗,则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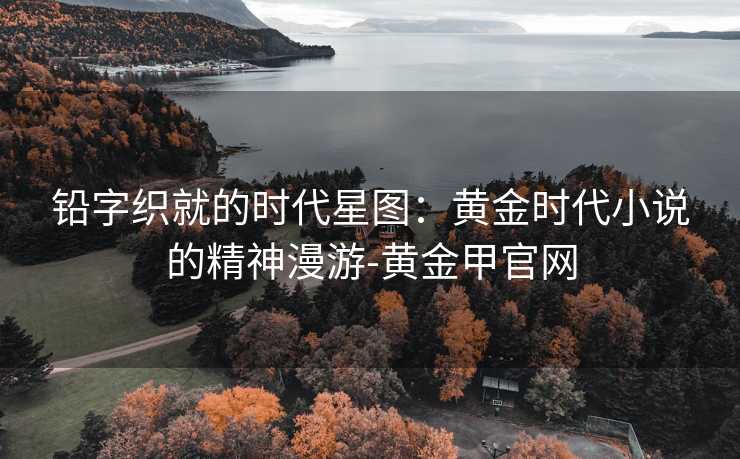
如今,当我们重新阅读黄金时代小说,依然能从中汲取力量。它们教会我们如何在喧嚣中保持清醒,如何在困境中坚守理想,如何在平凡中发现伟大。正如博尔赫斯所说: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而黄金时代小说,就是这座图书馆中最珍贵的藏品,等待着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去发现、去品味、去传承。
或许,黄金时代早已远去,但那些铅字所承载的精神,永远不会过时。它们将继续在时间的长河中漂流,照亮更多人的心灵,成为永恒的文学星图。